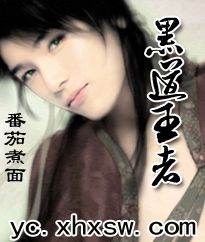正文 -- 第十六章 意外
我们身边,从不缺乏小人,他们穷极手段,厚颜无耻,一古脑儿,贪婪无度地往怀里扒拉着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。史太郎就是这种人。
我立下决断,整理仪容,换上笑脸,出了卫生间。花瓶女嗔怪说:“去那么久,还以为你掉马桶里了。”
我说:“实在不好意思,让大家久等。”
忠叔说:“幸好不在酒桌,否则罚你三杯。”
我说:“忠叔的酒量,上次领教过,自愧不如啊。”说话间,坐到位置上。忠叔说:“介绍一下,这位是史君,日本来的客人。这位姓陈,我们叫他阿来。”我起身和史太郎握手,说:“外国友人,欢迎欢迎。”
史太郎眯起小眼睛,说:“初次见面,请多关照。”
我说:“一回生,二回熟,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。”
史太郎笑眯眯的。
麻将开战,过程平淡无味,胜负不大,期间,史太郎和花瓶女眉来眼去,勾勾搭搭。临近钟点,忠叔接了个电话,貌似家里有事,大家提前散局,我关上房门,脸上笑容消隐不见,杀气腾腾,阴冷无比,在我的一生中,从没如此痛恨过一个人,直欲杀之而后快。
送悠悠回家的路上,悠悠问我怎么啦,发生了什么事,眼神好可怕,我忙说没事,跟人莫名吵了一架,一肚子的火。
回到出租屋,我打开电脑,找出电影《意外》,一口气看了五遍。人生诸多意外,显然某些人使用他们聪明的头脑,刻意制造出意外,不留痕迹地消除掉目标。我脑子里转过无数次的念头,无数的方案接踵而至,但一一否决。丽莎发来短信,问我去不去她那里。我说有事,去不了。我和衣躺在床上,七想八想,想着想着,睡着了。
我做了个梦,恶梦重现十年前发生过的一个个片断。出租屋里,我和飘飘欢声笑语,她调皮地将冻得红僵的手伸进我的衣服,我揉着她的头发,直到成了鸡窝……史太郎,宽边眼镜,深红西装,捧着玫瑰花,谦卑地笑,倚在他的丰田车旁守在飘飘上班必经的路上……飘飘回家越来越晚,曾经的恋人开始有了隔阂,有了吵闹……深夜,飘飘躲在被窝里悄悄地哭泣……大雨天,她从出租屋狂奔而去,粉红色裙裾高高地扬起一角,像只小鸟,逃脱出束缚她的牢笼,欢鸣着奔向更广阔的天空,回首的最后一眼,冰冷,决绝。
我蓦然惊醒,大汗淋漓,月光投进来,照在黯黯的床上,如此地惨白,如此地清冷,我仰起头,望着天花板呵呵呵地笑了起来。
之后一段日子,我改头换面,曲意迎逢史太郎。约他打牌,吃饭,洗桑拿,打保龄球,投其所好,极尽阿谀。钱和色,无疑是拉拢两个男人关系的不二法则。他几乎不设防地很快把我当成忘年之交,有些私人珍藏拿出来给我看,他手机里储存着各种造型,一丝不挂的女人,大多数是外国人,韩国,美国,英国,瑞士,等等,罗尽天下美色。我问他有中国的吗,他说有,滚动着手机屏幕,很快,一个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。
其时,我们泡在温泉里,两人赤呈以对,他举着手机,炫耀似的对我说:“陈君,她叫飘飘,我弄到手颇费周折,还行吧,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,秀色可餐。床上差强人意,有点冷淡,不过再冷淡的女性,用上苍蝇粉,乖乖就范。”
我迷惑不解地说:“这么多的女子,你全娶回家了?”
他故作神秘地笑笑,说:“玛尼,她们都是货物,在日本,女人是赚钱的工具,支那女人不值钱,欧洲女人最吃香,我把她们带回日本,玩腻统统地丢给乔治,他是山口组在东京的头目,生意顶呱呱。”
我对他竖起大拇指。
然后,我抬起膝盖,照着他圆溜溜的肚子狠狠来一下,他怪叫着倒在池水里,我揪着他的头发,按在水底下,作为朋友,我有义务让他的肚子趋于圆美,他尽情饮水的同时,我另一只拳头提得高高的,落得重重的,一记一记打在他的身上,打得他哭爹喊妈,祈祷日照大神快快来搭救。
没有然后,我以上全属空泛的臆想,我对他竖起大拇指,说:“史君,佩服,佩服。”
他不无得意地大笑,说:“哪里,哪里。”
再见丽莎,我抱怨地说:“你都认识些啥人,个人来路不正,花瓶女傍大款,背地里玩小白脸,官太太挥霍无度,她那花销如流水,老公逃不出一个贪,屎壳郎更无须说,简直一人贩子,就忠叔靠点谱,可他底子里不干净,指不定手上犯着人命。”
我们坐在她家的卧室的大床上,她披着睡衣,神情慵懒,拢拢头发,说:“看不惯上流社会呀。”
我说:“狗屁的上流,下流。”
她深情地注视我,说:“我就特欣赏你凡事不在乎的态度。”
她婷婷起身,缓缓地扯开睡衣带子,媚眼如丝,抬起一条腿,踩在床沿边儿上。她就有这么一种本事,让我瞬间跌入欲火的天堂,忘掉所有的杂念和不快。我迷失在她欲仙欲死的呻吟里。云雨过后,她娇喘吁吁,在我耳畔轻昵地说:“宝贝,做生意的,三教九流都得打交道,你反感他们,不来往便是,我们请个职业经理人,安安心心快快活活地过我们的两人世界。”我说:“我还没想好。”她似乎一下子把我看穿了,说:“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。”我说:“没有。”她情绪低落,说:“你不信任我。”我说:“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,问题在于有的事你不能参与。”她失望地说:“还是有事瞒着我。”她翻了个身,屁股对着我。我推推她,说:“生气了。”她硬梆梆地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:“睡觉。”我大睁着眼,情景何等地相似,与林雪闹别扭的那夜,因果循环,报应不爽。
迷迷糊糊间,她反过身来趴到我上面,轻轻地吻着,从我的额头到脚尖,细致不漏地亲吻过每一块方方寸寸,我全身麻痒,莫名地感动,然后,她与我嘴唇对着嘴唇,鼻子对着鼻子,眼睛对着眼睛,她的脸庞呈现奇异的光彩,她说:“宝贝,答应我,无论如何,莫做蠢事,别让我担心。”
我凝视着她如钻石般褶褶发光的眸子,说:“好。”
我说好字,仅仅身体生理机能的本能反应,张开嘴,胸腔挤压,舌头不抵天花不靠牙床,气流自口腔一泻而出。好字出口,我的心沉浸在黑暗里,黑暗里荡漾着莫以名状的忧伤和难以言诉的自责。我沉溺在低迷的情绪中难以自拔,如果,当年我再加把劲,再对飘飘好点,或许她会心软留下,或许事情会是另一种样子。她把生命中最美好最珍贵的给了我,我却给了她羁绊和失落,最终导致可怜又可悲的下场。没有如果,只有因果,当年的我,写过一首歌,关于飘飘的背离,歌名《叹月》,叹一声,当年的你,迎风而舞,飞上了九天。寒夜里,你容颜依旧,只是无人再来欣赏你的美。原来结局早已注定,背弃了誓言,只留下千年的冷清。站在彩云环绕的月亮之巅,你的脸上,为何写满了落寞。遍地月色,无边无际,是不是你追忆的目光。
黑暗中,丽莎发出轻微的睡息,而我,睁大着眼睛,泪水悄悄滑落。
生命是什么,生命是父亲母亲在某个风雨之夜宣泄欲望带来的后果。
父母离异后,父亲看我的眼神,似极度懊恼,在那个原罪之夜,他为什么不把我射到脏乎乎的墙上。
一个颓废的老男人,从我稚嫩的小脸上看到令他屈辱的女人的影子而迁怒于我,非常地不合情理,他应该憎恨那个年代,人们贫穷得连避孕套都没听说过,找个塑料袋也十分地不易,他更应该憎恨自己的草率,娶了命里犯冲相克的女人,他的偏激,使得他把人生境遇的不幸扩大到整个人生的灾难,在我三岁时选择离家出走,从此杳无音信,母亲不久后改嫁,远远的三千公里以外。
我由爷爷一个人带大,关于童年最深刻的声音是,冬天凛冽寒风刮过门前杨树树梢的尖哨,尖哨声甚至刺入我的灵魂,让我在其后的无数个寒冷或者不寒冷的夜晚不战而栗。
那时,村子里的人歧视婚姻不幸的家庭,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跟我玩,我经常形只影单,走在荒凉的田野上,张开嘴,哈地长长地吐口气,从气流里,我听到了千军万马,冲阵厮杀,热闹非常,年少的我,过早地品味到人生的寂寞和苦闷,我心里暗暗发下一个誓言,绝不步父母的后尘,一生只爱一个,没有吵架,没有欺骗,没有背叛,一旦结婚,决不离婚,死也不离。
飘飘,我的最爱,也是唯一一个为我打过胎的女人。在香城那个阴暗狼狭小的诊所,我亲眼见证一个无辜小生命的过早凋零。她融化了母性光辉的满脸的泪,使我陡然成长,我对她百般呵护,为此,准备消费掉一生的时间。而现实最终用更响亮的耳光回敬我,我失去了她,永永远远。
秋天,又见秋天。透过车窗,香城郊外落叶满地,无比萧索。
我挤在班车里,顺着国道朝南一直走,途经六座县城,下车时,离国境线不足100里。街头觅辆三轮,给他双倍价钱,好说歹说,他终于首肯连夜拉我进山,蜿蜒崎岖约三个小时,巅跛辛劳自不待言,车子走到实在走不动,我下车步行。典型的喀斯尔山貌,有些路面,侧面便是万丈悬崖。山路难行,走一段,歇一段,手中药箱重达千钧,拂晓,找到了这个叫“猫跳峡”的村子。
相关媒体报道过“猫跳峡”,它因全村贩毒吸毒,感染爱滋病,劣迹斑斑而名嗓一时,村子破落不堪,死气沉沉,我套上白大褂,提着十字药箱,走进最边上一家院子。院门开的,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,只存在于两种现象,一种民风淳朴,一种极度贫困。
我站在院子里,大声地喊:“有人吗。”
堂屋的门吱呀一下开了,颤巍巍的,现出一个男子,眼窝深陷,骨瘦如柴,眼珠子瞪着人,不像瞪着人,视线穿过人的身体落在虚空,死鱼样失去了神采。
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红本,在他眼前晃了晃,说:“你好,我是世界aids研究学会区域血样采集负责人,这是我的证件,请过目。冒昧问一下,你是感染者抑或病患者。”
他不闻不顾,手扶着门,好似随时要倒下来似的,他虚弱至极,看上去快死了,或者,他已然死了,精气神全无,只剩一具空壳。
我心下了然,打开药箱,里面现出一根针管,问他:“可以吗。”
他轻飘飘的吐出,钱。
我数出三张大钞,放到他手里,他裂了裂嘴,坐到门槛上,撸起袖管,皮包骨头,筋络如蚯蚓,历历在目,上面密密布满针眼,我将针头轻轻压进血管,只抽了一点儿,此人眉头皱也不皱一下,司空见惯的神情。
我小心翼翼将针管放入恒温小箱,吐口气,说:“省点花,多买点补品。”
他默默地进屋,恍若未闻。在他的眼里,我空气一样,出现了,又消失了,不曾留下任何印迹。他身体的机能被毒品和病患折磨得紊乱退化,我怀疑他是否记得我这么个不速之客,我的样子,我说过的话,我做过的事,他手里的钱从何而来,当然,它很快会变成一小撮粉末。
我回到香城,装作没事儿似的。一夜无眠,在天台上坐一宿,快要天亮,草草打个盹,时节已至深秋,在老家这个时候,落叶铺遍大地,香城很难体会到深秋苍凉意境,放眼而去,一大片一大片地青翠,落叶也是青翠, 有阳光的天气一律暖和,遇雨而冬,香城一大特点。
这时,我多想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,将这个不知寒暑的城市里里外外洗涤一遍,多想冲进大雨里,全身上下痛痛快快地浇个透,冻得嘴青脸白浑身打摆子便又如何,怎及我内心深处的酷寒。我准备好一切,走出家门,走出城中村,走过星棋罗布的街道,走过缤纷妖娆的公园,走过欢笑的人群,走过拥挤的天桥,走过清澈的湖水,走过十字路口,绿荫掩映下,会所到了。
四个人,人数刚刚好,时间刚刚好。花瓶女,官太太, 史太郎,我。 官太太说:“我们开始呗。”
花瓶女说:“阿来,丽莎不在,你的胆子越来越大,敢独挑大梁,有魄力。”
我说:“我要捞本,自从史社长来了,我的运气不怎么顺,他是我的克星。”
史太郎干笑着,说:“赌桌上有胜有负,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。”
说他胖,他还喘上了,若不是我有意放水,他输是连他妈都不认识。趁着麻将机洗牌的工夫,我去冰柜里取饮料,问两女的喝啥,她们要露露,我接着问史太郎,他说老规矩,我从酒柜里拎出一瓶法国干红,开瓶启退着木塞,打趣着说:“史社长,打玩麻将饮红酒,你这口味够独特的。”
史太郎和两女的说着话,没空搭理我。我背对他们,酒架上摘下高脚杯,倒酒,袖口解开,腕骨上透明胶条封着一段塑料管,小指弹去堵口,精心准备的红色液体神不知鬼不觉地和着红酒注入酒杯。
花瓶女说:“阿来,快点。”
我说:“来了。”
高脚杯稳稳搁至史太郎身边的茶几上。我坐下,意气风发地说:“小弟今天子弹充足,诸位,尽管放马过来。”
我的子弹为史太郎而备,目的让他得意忘形,忘乎所以。在我暗地里为他送牌的情形下,他战果斐然,小眼睛眯成一线天,花瓶女噘着嘴,官太太眉毛直跳,史太郎数度端起酒杯,又放下。喝吧,喝吧,我心里有个声音不断地说,喝下去,你和我,我们大家都解脱了。不日,你将病毒发作,性免疫综合系统失调 ,全身疲劳无力,食欲减退, 发热,体重减轻,随着病情的加重,各类皮肤感染,渐渐病毒侵犯内脏器官,持续性发热,腹泻便血,各个组织器官散发恶臭,你将为世人所唾弃。
史太郎嘴里念念有词,似在祷告,看得出,他听牌了,而且是一副大大的好牌。
轮到他摸牌,他抓过一张牌,捏在手里,左看右看,举止古怪。
花瓶女不耐烦,说:“打呗。”
“胡了。”史太郎推倒牌,他手舞足蹈,哈哈笑个不停,说:“绝世好牌,双龙背。”
花瓶女和官太太脸色剧变,花瓶女叫道:“麦麦撒撒。”她眼光扫过牌面,吃惊地捂住樱桃小嘴。史太郎太高兴了,脸上笑得有些变形,笑着笑着,口眼歪斜,顺着椅子溜了下去,人事不省,他中风了。
我猛然起身,指点着史太郎,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尔后,我放声大笑,传说中笑出腹肌的大笑,史太郎的乐极生悲,我的歇斯底里的大笑,搅得俩女的神经错乱,目瞪口呆,她们大概以为我疯了,拉扯开房门,对着外面扬起噪门高呼:“快来人呐,救命啊,救命啊。”